戴锦华:姜文在嘲弄社会主流逻辑
《一步之遥》作为“颠覆再现的再现”,和我们整个时代、和今天中国是错位的。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这部电影,理解姜文。我对他的这种由衷的认可和尊重延续下来了。它不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它由于多重错位注定要在资本运作、资本市场上失败。

采访人:滕威,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对话戴锦华:〈简爱〉的光影转世》等。
受访人:戴锦华,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专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雾中风景》等。
没有“第七代”,可能也不会有“第八代”的电影人
北青报:最近您出版了自己的电影研究的学术自选集《昨日之岛》,印象中这好像是您第一次出版自己的自选集。文集中收录的文章,比如《断桥:子一代的艺术》、《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等都是在海内外影响十分广泛的论述。但是这种代际的划分,如果用来描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是否仍然有效?我看到一些影评人在谈“第七代”,您觉得“第七代”存在吗?
戴锦华:我可能会重复我的错误。当年我就否认“第六代”,这种否认包含一种期待—我们的历史不再如此特殊,如此差异,如此充满断裂性的激变。我之所以否认,是因为关于中国电影的代际论述中有着清晰的历史原因。所以,当时我就希望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更深地融入到全球化过程当中,电影导演是通过他们的个人风格、用自己的作品来命名自己,而不是通过某个年龄段,甚至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某一批学生来获得共同命名。现在我还是要重复我的“错误”,可能不会再有一个用代际命名方式来形容一个电影群体。我想说的是,没有“第七代”,可能也不会有“第七代”或者“第八代”的电影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一种悲哀,因为我们“第四代”、“第五代”其实是作为“中国电影新浪潮”而形成的,这个命名既是突出他们的代际特征,更是标志了一种新的电影美学革命,一种全新的、群体性的、新人辈出、佳作辈出的年代。现在中国电影工业规模的扩张幅度已经是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每年都有大量的年轻导演和他们的新作出现。但是,我必须说,这些年轻导演没有向我们或者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姿态。其实,如果有代际的话,我希望是那样一种代际:新人辈出、佳作辈出,风格极端多样和丰富。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期待着这样一种中国电影的崛起,而且我更希望这是由年轻一代导演所代表。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判断吧。
姜文完全不能被代际所划定冯小刚接近中国三十年代城市电影
北青报:您刚提到所谓“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是围绕北京电影学院来进行命名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导演,他既不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也没有办法被放置在原有的代际描述的格局当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直到今天,他始终是中国当代电影中独特另类的角色。您在很多场合,都一向激赏姜文的作品,那您怎么看姜文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独特位置?
戴锦华:确实,姜文在某种意义上说始终是极端特殊的。如果我们一定要用形容词,大概是用“天才”,或者是“特立独行”去描述他,姜文在当时既存的中国电影体制之外,他其实是一种个人化的创作,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作者电影”。特吕弗所倡导的“作者电影”—即以自己的个人风格、以自己的生命际遇,顽强地,固执地直视自己生命深渊式的心理体验,并且试图去展示它、回答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确实没有另外一个导演可以和他相近。他是完全不能被代际所划定的一个导演。
另外一个和他完全没有相似性的导演,就是冯小刚。在年龄段上,他也是“第五代”的,但从开始创作的时间看他是“第六代”的,他以商业性、通俗性、都市娱乐性著称,他全盛时期的电影其实更接近中国三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电影,那样一种谐谑的、通俗的,而且曾经是受到底层人认同的作品。
北青报:姜文以前给人的印象是电影市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坚持自己的社会思考和艺术表达。但从《让子弹飞》开始,姜文变得关注票房和市场了。那句很豪放的“站着就把钱赚了”的宣言和挑衅,不仅表明影片大卖,而且还表达出他不妥协的立场。可是接下来的所谓“三部曲”的第二部《一步之遥》预期票房二十亿,但现在只有六亿,差之千里。尽管在2014年的国产片中,六亿的票房不算惨。可是它所遭遇两极分化的评论,恐怕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当中非常罕见的。我个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这种两极评价当中,我很难清晰地把握到思想与艺术立场差异的逻辑延伸。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在今天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遭到这样不堪的境遇?
戴锦华:在姜文的电影序列当中,叫好又叫座的《让子弹飞》是一次例外—毫无疑问,这是所谓业界良心之作,但它已经不具有姜文作品一以贯之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一步之遥》是姜文对他的艺术自我、他的作者电影诉求、标志风格的回归,但是这是再一次的全面失利。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这是2014年最重要的中国电影。
《一步之遥》引发了整个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介入与关注。而且非常奇特的是:阵容清晰,无保留支持姜文的大致都持有某种社会批判立场,而这种立场又同时具有相对清晰的左翼色彩。整个影片极端尖刻嘲弄的社会逻辑,其实是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主流逻辑。他毫不留情地嘲弄的种种丑陋猥琐,其实是今天世人所崇尚和奉行或者是自我包装的逻辑。例如说“We make the history”,我们创造历史,我们置身历史之中。比如说,他让妓女花国总统站出来大讲“苟日新,日日新,每天太阳都是新的”。所有这些逻辑其实是今天最主流的、最能媚俗的逻辑。对这部影片高度认同的影评人大都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感到极度的酣畅淋漓,影片诱发他们发自心底的快乐,所以在他们看来这部电影是极端成功的。
《一步之遥》让我由衷认同但仍无法进入
北青报:您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谈到了几乎2014年所有重要影片,唯独没有对《一步之遥》公开发表过比较详细全面的论述,您在刚才对它所作的正面肯定之后,接下来要说“但是”了吧?
戴锦华:不急。在“但是”之前,我还有话说。首先,大概是在几个层次上,我充分肯定这部电影。一个是刚才说的制作规模。如果说中国电影整体的工业水准有待提高,那么这部电影应该作为某种标准或者某种示范而受到肯定。电影对每一个场景的营造,对每一个场景带有视觉奇观、艺术意象性的原创,而且同时是用视觉意象去营造社会整体的荒诞性,极为突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有人认为类似这样的表达会让你想到库斯图里卡这类后现代的荒诞主义艺术电影大师。但是实际上,姜文只是在某种情调上或者氛围上让你有这样的联想。姜文和他们没有任何雷同。其次,非常清楚,这是一部“元电影”。
北青报:对,这也是我特别欣赏《一步之遥》的重要原因。
戴锦华:中国电影别说在如此大制作的电影上没有过一部成功的“元电影”,小制作上也没有。它在多个层面上成为一个“元电影”,自觉的“元电影”书写,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它是根据阎瑞生的故事改编而成,阎瑞生的故事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故事长片之一。而我自己曾在做电影史的时候非常迷恋围绕《阎瑞生》这部故事长片所形成的历史的和电影史的事实。没有比围绕这部电影的事实更让我体认到世纪之初、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之后,作为新兴移民城市的上海的现代性和充裕性。花国总统被当时的白领或花花公子所谋杀,这个谋杀案怎样成为了系列的全程跟踪报道,引发病态的兴奋和关注,阎瑞生还没被缉拿归案,同名舞台剧已经上演;舞台剧又是以舞台奇观而著称的。和影片中的王天王不同,当年的舞台剧是以将阎瑞生作案的车的实物搬上舞台著名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舞台是多么摩登。后来迅速被改编为电影,而电影当中的主要角色是找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小姐妹来扮演。它是个故事片,又或者说是商业奇观,同时也是最大程度榨取一桩血腥暴力的谋财害命都市案的商业价值。这极端丰富质感的电影史事实让我当时十分迷恋。这次,姜文是对这部今天已经不存的、我们无从看到胶片的、对其影像一无所知的电影史名片的整体重拍。
第一时刻我们就意识到其后现代重拍的特质就是对《教父》的戏仿。最华彩的段落是模仿早期默片十六毫米的段落,武六制作的《枪毙马走日》的默片段落,在好莱坞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歌舞片的段落场景,这同时构成了电影多层次的“元电影”特征。不仅如此,电影当中还包含了电影制作行为;武六制作的马走日的荒诞的、戏剧性的生命遭遇的段落;和武六制作枪毙马走日的电影的过程。他用“元电影”的方式重现了电影史的现实,就是他们如何逼迫马走日来扮演马走日,在他电影中扮演马走日来换得活下去的机遇,而最终迫使马走日显现他生命的底线。这是这部电影非常突出的成就。
我之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对这部电影表态,是自己无法说明我对这部电影的观影体验。这是2014年我最期待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2014年我唯一期待的电影。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观影感受很复杂,或者可以说,我的观影经验非常的流俗。电影的开篇,电影的延伸,极大地满足了我的预期,我高度地认同和进入了这种尖刻的喜剧感。但是到了歌舞片的场景,就是白虎接承了青龙的段落继续延续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清晰的感受:我无法进入这个电影。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它的影像仍然吸引着我,它的对白,也就是每个段落中大量的对白让我由衷的认同,产生真的共鸣,但是我仍然无法进入这个电影。
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我不仅被吸引,而且很多时候被感动。在《一步之遥》当中所有的吸引带着迷惑,同时呢,我始终没有被感动。第一次,我对于姜文电影的叫骂者,想从某种程度上去理解。
长时间结构性地延续观众的焦虑势必造成观众愤而离场和郁闷不止
北青报: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想听您的解释。
戴锦华:我想我大致找到某种解释,一是这部电影的原创性和艺术成就应该加分。因为整部电影结构性地形成了一种“反缝合体系”式的剪辑。电影绝大多数的场景内部,有一个舞台式的结构设置,不用说花国选美的这个场景直接形成了一种“舞台下的观众”的场景结构,第一场戏仿《教父》,前景当中焦点之外的马走日已经处在了某种观众的位置上,而武七在中景当中奋力表演。在绝大多数的场景画面当中,姜文同时设置了表演者和观看者的视点。我们可以从很多电影当中看到这种舞台式的空间,关键问题是,姜文的所有场景中,舞台性的空间当中观众席是另一个舞台,观众席上的观众在“表演”—完颜英是从观众的舞台中发言并且跳上舞台的,而同时武六在观众席上架摄影机,以导演的身份、在导演的位置上去拍摄舞台上的表演,它在每一个场景当中形成了多重“观看与被看”的结构,或者说,在每一个场景当中它完满了一个自足的“观看与被看”的结构。它就与绝大多数电影中会设置一个观看的位置给观众、让他们去观看广义舞台上的演出的结构有极大的偏离和不同,因为《一步之遥》内完满的“多重观看与被看结构”事实上封闭了银幕的幻觉空间。
另外,这部电影原本有一个充裕的商业化的设置和潜能,就是“两女一男”,大家闺秀和风尘女子,一个男人被风尘女子暗恋,而他暗恋着大家闺秀,这其实有一个非常现成的、清晰的情节剧故事架构,有足够的狗血可以洒,但姜文抑制了这个剧情结构,他选择了马走日作为单一的主角,然后这两个女人只是他生命中的“偶遇”。于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尽管有完颜英的“会错意”,有完颜英固执地求婚,最终这导致了完颜英的死亡;然后有马走日和武六之间近乎荒诞情节剧式的、被踢断两条腿的“前史”,以及最后武六以死相争来试图拯救马走日的剧情结构。但由于影片设置所有这些人物是马走日生命当中荒诞遭遇的一部分,就形成了男女主人公之间非对切性的、非匹配镜头的视觉组合。比如说武六闺房中的那一场,也就是所谓的“机器人”,所谓的“当年火车上的遭遇”,它使场景高度的舞台化。场景高度的舞台化之后,男女主人公之间原本可以有的深情戏、或者可以说带荒诞色彩的深情戏场景,就变成了一个表演性的场景,一个朝向不在的观众的表演性场景,而没有形成两个人之间的相互观看,所以这两种东西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表述:一边是多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封闭了、自足了幻觉空间,以致观众无从进入;而另外的一重关系就是一个舞台化的空间去抹除了人物之间的匹配镜头所形成的人物之间的这种视觉的连接,就是所谓“目光纵横交错”的段落。
通常,“反缝合体系”的使用是通过不提供反打镜头,不提供观看者的位置来造成一种观众无法进入影片、无法获得自己主体幻觉的巨大焦虑。而这部电影当中它是通过这种影片内在的、多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来完成这种自我观看的锁闭,把观众排除在其间,这本身是一个原创性的“反缝合体系”的表达。
“反缝合体系”当年不仅是作为艺术电影,而且是极端的先锋电影的实验所形成的视觉颠覆,它要达成的效果是制造现实焦虑。因为主流电影的最大的社会功能就是平复资产者和中产者的现实焦虑,然后成功地创造、完满他们的主体幻觉。所以六十年代激进的批判者说“我诅咒电影诞生的日子”,电影诞生的日子是文化最黑暗的日子。原因就在于电影可以成功地维系、消除现代社会、现代人、现代性所制造的这种巨大的焦虑感。而先锋电影或实验电影就是通过制造焦虑感来再度暴露被电影、被娱乐、被现代文化、被消费主义所抚慰的这种焦虑。
这部电影片长两个小时二十分钟,你用这么长时间在结构性地延续观众的焦虑,势必是造成愤而离场和郁闷不止,我认为这是这个影片票房失利的内在原因。如果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我应该无保留地认同姜文的。我们应该为姜文成功制作这样的一部电影而感到骄傲,或者说为他大声喝彩,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孤独地为这部影片大声喝彩。
但是当这部影片和它的巨大的资本投入以及围绕这部影片的大规模的商业的营销所建构的预期来比,它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层次的错位。它其实提出的问题比这部电影更加深刻: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个大资本的手段去质疑大资本?去解释在这个大资本涌流、不差钱的时代背后那种巨大的文化荒诞?以及它事实上制造的、我们每个人在现实当中的、每时每刻的生命焦虑?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完成这样一个矛盾的命题?
大量对白和华美饱满画面同时倒塌本身就是对消费文化的再现
北青报:您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戴锦华:至少《一步之遥》的票房实力以及它所造成的这样一个恶骂的局面来告诉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一切都建筑在资本的奇观—一种原创性的、无所不在的、入侵式的广告所建构的巨大的社会期待/心理预期的情况下去揭示,人们期待在电影院片刻遗忘和缓解资本逻辑所造成的焦虑,结果你遭遇到的是对这种焦虑的原创性的、成功的再现,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观众的愤怒,我理解那些愤而退场的人们,而且我也理解这部电影为什么获得了左派的喝彩。原因可能在于,那些即刻对这部电影完全认同和由衷大声喝彩的人们是由于他们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外在的主体”,他们无需电影来召唤出幻觉主体,他们完全认同了姜文叙事和表达自身的批判,影片所制造出来的观影焦虑完全影响不到、不伤及他们的主体位置和已然形成的对这种焦虑的批判和指认。
北青报:您这个解释我很开心,我姑且认为自己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是自己“主体强大”。您另一层面的解释呢?
戴锦华:在最早观影的时候我就为精彩的对白而欣喜。“To be or not to be”变成了“这么着还是那么着”,这种喜剧感,这种快乐从第一分钟抓住了我。接下来每一段落都有大量的对白、金句让你非常会心。可是,它仍然没有让我过目不忘,因为把“To be or not to be”翻译成这样是姜文半生的玩笑,就是他化解了哈姆雷特的那种生存还是死灭的两难。其他的,看过之后,我很难重述。于是我意识到另一个不能让我进入电影,让我无法获得观影快感的原因是:大量的对白和极端华美的饱满的画面同时倒塌。而从这一方面,姜文又在挑衅和违背一个电影构成的基本原则—通常旁白进入的时候我们会给全景镜头,因为画面是空的,声音就可以进入。但当画面高度富丽、饱满和奢华的时候,旁白的密集出现使其过度超载。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我们知道姜文当然不是不懂得对白与画面之间的关系,只能说这部电影他是刻意地制造这种效果,就是一种过剩的、无从负载的、无从选择的、看画面无法听对白听对白的时候就忽略了画面,旁白整体削弱了画面奇观的视觉冲击力,而画面奇观排除了对白、旁白所负载的极端丰富的社会信息。你可以说这是影片整个结构性的错误,或者是结构性的失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这种过度表达,和极度过剩的感觉本身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再现。
北青报:所以您觉得,《一步之遥》生不逢时。
戴锦华:对。影片作为“颠覆再现的再现”,和我们整个时代、和今天中国是错位的。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这部电影,理解姜文。我对他的这种由衷的认可和尊重延续下来了。它不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它由于多重错位注定要在资本运作、资本市场上失败。这是我对《一步之遥》的看法,我始终没有对它表态是因为我无法对它表态,因为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去判断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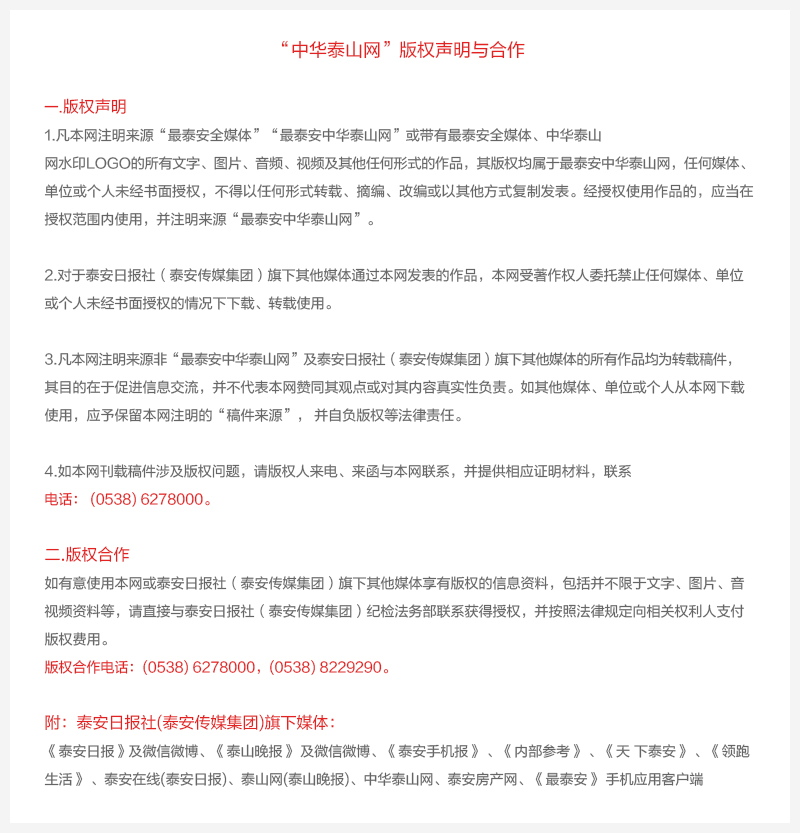

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主管 泰安日报社主办 地址:泰山大街333号泰安传媒集团22楼 联系电话:0538-6272000 邮编:271000
中华泰山网 版权所有:Copyright ? my0538.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鲁B2-20100031号 鲁ICP备08005495号-1



